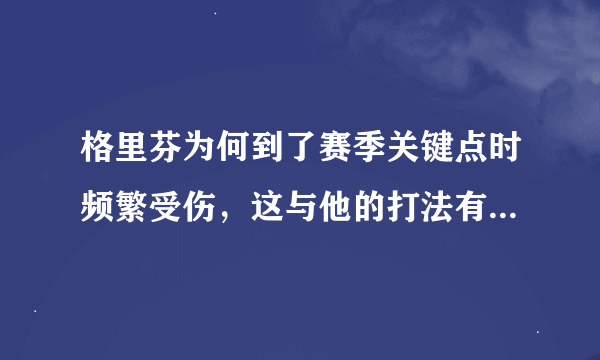格里高利的悲剧原因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造成格里高利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他的哥萨克身份。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哥萨克”泛指15-17世纪俄国从农奴制压迫下逃亡出来,迁移到边远各地的农奴、仆从和市民。从16世纪开始,哥萨克因替沙皇政府镇守边疆,被免除劳役和赋税,并获得一定的奉禄和土地,同时哥萨克形成了带有相对自治性质的组织,他们是沙皇兵力的主要来源,18世纪开始成为特殊的军人阶层。特殊的历史一方面使哥萨克保留了许多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酷爱自由,粗犷善战。可以说,哥萨克最大的矛盾是:内心向往自由,身份上又是沙皇镇压自由的工具。格里高利就是在矛盾的哥萨克环境中成长起陵碰来的一个青年哥萨克的代表,他有责任感、有良心,有哥萨克特有的群体归属意识,也有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 哥萨克自身的矛盾性决定了格里高利的迷惘:是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许诺给受压迫者以自由;还是选择哥萨克,因为自己世世代代身为哥萨克。就这样,格里高利是千百万在红军和白军犹豫不决的哥萨克的缩影。正如格里高利所属的那个白军师的师参谋长考佩洛夫所说:“一方面你是一个拥护旧时代的战士,另一方面请原谅我说话尖刻,又有点象个布尔什维克。” 造成格里高利的悲剧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又不仅仅是个哥萨克,而是一个善良的、有良知的人。与他那些甘心被白军挟裹的亲戚朋友不同,格里高利除了哥萨克效忠沙皇的原则之外,还有自己的原则--良心,还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珍惜人类生命。所以,当他第一次看白军滥杀俘虏,就勃然大怒,几乎杀了凶手“锅圈儿”。此后的战役中,格里高利目睹了双方的残酷行径,虽然为了生存,自己也要不断地杀人,并且获得过白军颁发的四个乔治勋章和四个奖章,升为白军师长,但在他的内心世界,他一直痛恨杀人、特别是无缘无故地滥杀俘虏--无论是对红军还是对白军。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对战争渐生厌倦,几次想放下武器袭汪猜。但是社会与时代的具体环境又迫使他一次次重新拿起武器。于是,格里高利的心灵运动始终建立在内心的矛盾与斗争之中:他厌恶白军的腐朽反动,又对红军的过激行为不能容忍。而在具体行动中又始终处于无可奈何、无法选择的状态:在克里摩甫斯基战役中,他勇猛地挥刀砍杀,之后又趴在地上大哭起来:“我杀死的是什么人呀?为了上帝,砍拍型死我吧。”在1920年他回到家乡,却因为遭到红军政权的怀疑而再次当上了叛军。格利高里的徘徊动摇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个人的主观原因。格利高里出身于中农家庭,就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来说,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其政治特点是左右摇摆。格里高利作为一个哥萨克军官,他的左右摇摆则以更加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农的私有观念和哥萨克军官的特权思想,在他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间横着一条深沟,使他把苏维埃政权看成异己的政权;而劳动者的朴素感情和平等意识又使他同白匪军格格不入。他本能地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企图寻找一条超越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道路;落后愚昧的哥萨克传统生活习惯和中农的小生产方式造成他目光短浅,政治幼稚,使他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分不清是非善恶,他怀着哥萨克军人的雇佣思想时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时而为反动势力效劳。他以资产阶级庸人观点看待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把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看成毫无意义的仇杀,既无法理解革命政权对反动势力的无情镇压,也厌恶反动势力对革命战士的野蛮摧残,他天真地认为革命和反革命可以“和平共处”;哥萨克军官的狂妄自信、粗野任性和冒险精神使他在动荡的年代不甘寂寞,顽固拒绝接受生活的真理,直到碰得头破血流才肯罢休。格里高利的艺术形象真实地概括了哥萨克中农的本质特征,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个性,它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和社会环境中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 格里高利的悲剧不能只归因于其性格的摇摆性,同时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来说,其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也决定了他在那个年代必将走着一条坎坷的道路,同时也应看到那个动荡时代对其的影响。试想一个独立、渴望自由与真理的人生活在一个无法找到独立和孤傲的世界里,这便是格里高利性格的悲剧之所在。